论“刺死辱母者”案一审判决的正当性 ——勿让舆论干预审判,勿让情理代替法理
浏览量:时间:2017-03-26
论“刺死辱母者”案一审判决的正当性
——勿让舆论干预审判,勿让情理代替法理
作者:王文文(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这两天被《刺死辱母者》的消息霸屏,舆论一边倒,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僵化,对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于欢构成正当防卫的辩护意见不予理会。一审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有违伦理和道德,而伦理都可包容的行为却不能被法律包容。舆论认为“在法律调节与伦理要求的行为之间产生冲突,需要法律更多地正视这些人心经验”。
联想到一直耿介的“药家鑫案”。彼时,药家鑫撞人后舆论将药家鑫描述为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并毫不掩饰地直接在标题中使用这些词语,塑造药家鑫的形象,直接把药家鑫的家庭塑造成了特权阶级,激起民众更大的愤怒。至此,全国“杀”声一片,皆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矛头直指司法机关要求杀人。如民意所愿,2011年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然而药家鑫当真罪大恶极到必须以死赎罪?

民众们毫不犹豫地对药家鑫进行道德审判,其实包括太多的社会精英,他们掌握着话语权,但是却缺乏对所有事实、对法律基本的认识。
此时,民众又毫不犹豫地对聊城法院进行道德审判,对本案的事实进行道德绑架式的评议,认为聊城法院错判,于欢在母亲被辱的情况下刺死辱者应是正当防卫,且量刑过重。难道聊城法院的判决当真不合情理、不合法理吗?
根据网上公布的判决书以及南方周末的报道,先看本案的事实:
1、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被限制在公司财务室,由四五人看守,不允许出门。“在他娘俩面前,他们用手机播放黄色录像,把声音开到最大,说的话都没法听。”于秀荣说。
2、当晚8点多,催债人员杜志浩驾驶一辆迈腾车进入源大工贸,将苏银霞母子带到公司接待室。接待室内有两张黑色单人沙发和一张双人沙发,苏氏母子分别坐在单人沙发上,职工刘晓兰坐在苏银霞对面。11名催债人员把三人围住。刘晓兰说,杜志浩一直用各种难听的脏话辱骂苏银霞,“什么话难听他骂什么,没有钱你去卖,一次一百,我给你八十。学着唤狗的样子喊小孩,让孩子喊他爹。”
3、其间,杜志浩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嘴上。刘晓兰看到母子两人瑟瑟发抖,于欢试图反抗,被杜志浩抽了一耳光。杜志浩还故意将烟灰弹在苏银霞的胸口。让刘晓兰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杜志浩脱下裤子,一只脚踩在沙发上,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刘晓兰看到,被按在旁边的于欢咬牙切齿,几近崩溃。
4、接待室的侧面是一面透明玻璃墙,在外面的一名工人看到这一幕,赶紧找于秀荣让她报警。当晚,于秀荣老伴的电话一直拨不出去,他走出去几百米,才打通了110。22时13分(监控显示),一辆警车抵达源大工贸,民警下车进入办公楼。
5、判决书显示,多名现场人员证实,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4分钟后,22时17分许(监控显示),部分人员送民警走出办公楼,有人回去。
6、看到三名民警要走,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于秀荣回忆说。而警方的说法是,他们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
7、这期间,接待室内发生骚动。刘晓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看到警察要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了下来。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出一把刀乱捅,杜志浩、严建军、程学贺、郭彦刚四人被捅伤。最终导致杜志浩失血性休克死亡,严建军、郭彦刚重伤,程学贺轻伤。
一审判决:关于被告人于欢的辩护人提出于欢有正当防卫情节,系防卫过当,要求减轻处罚的意见,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欢持尖刀捅刺多名被害人腹背部,虽然当时其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辱骂和侮辱,但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母子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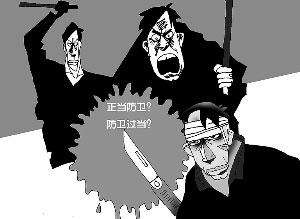
《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我想大家都明白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于欢不是在自己或母亲遭到侮辱和辱骂的当时反击,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结合当时案情和正常人的心理,可能是于欢觉得警察将要离开,他和他的母亲将有可能再次陷入不法侵害。然而不论是不法侵害结束还是将要进行,都不是适时防卫,都不是正当防卫。
至于被害人对于欢和于母的非法拘禁行为,由于非法拘禁是持续犯,从限制人身自由开始到解除整个期间都属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可以进行有限度的防卫。针对此种观点,我亦赞同,只是警察的到来是否可以认为是非法拘禁这种不法侵害已经解除了现实危险?一审判决在此点上值得商榷,毕竟警察的行为没有给于欢这种危险解除的安全感。但于常理来说,一审法院的理解不能说就是错判了。
亦有人认为,被害人对于母的辱骂和侮辱情节之恶劣,可以认为是“行凶”,暂且不论这种定性是否可取,即使是无限防卫,也要求“正在进行的行凶”,前文已述随着警察的到来,“行凶”已经结束,这样是无法认定为无限防卫的。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本案中于欢的伤害行为,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一人轻伤,这样的后果已经非常严重,而聊城法院也考虑到被害人的过错等因素,对其判处无期徒刑,这样的量刑并无不当。
本案让民众愤懑的与其说是法院的判决,倒不如说是警察的渎职。对被害人的非法拘禁行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等行为置若罔顾,只一句“不要打人”了事,如果警察对被害人们追究上述责任,悲剧就可以不发生。
我们很多人都是在严苛的构成要件论的刑法学中成长,我不例外,法官应该也是如此。再加上司法实践中认定正当防卫简直太难,依着这样的惯性,聊城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突然而至的舆论、民情让本案处在风口浪尖,一审判决成为民众抱不平的出口。
不得不说,在没有更多证据材料的支撑下,作出这样的结论是我的僭越。无论判决正当与否,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中,此事的出现或许正及时,以后法官们审理案件或许会慎之又慎,终于可以本着良心公平公正判决;或者让人更加担忧,法官们再也不敢独立审判。
孟德斯鸠说,有两种腐化,一种是由于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人民被法律腐化了。道德的腐化或法律的腐化,大抵如此。如是为个案权衡、利益权衡,尚可,真正难办的是“情大于法”的伦理信念,这是法治的困境。
诚然有诸如“许霆案”、“张金柱案”、“张君案”、“邓玉娇案”等一系列案件,都与媒体及民间舆论有关,其中多数监督产生积极影响,弱者正是通过监督由“地位”的弱者变成了“舆论”的强者,最终讨回法律的公道。但是法律是不应该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更不应该被外界的压力所左右。如果大众的舆论真的是民心所向和符合客观实际,那么我们应当拷问的是法律的公正和判决的合理性,而不是顺应民意、舆论。如果每一次案件需要经过这样的舆论公审才能纠错、才能公正,这无疑是司法的悲哀。

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调查于欢故意伤害案了,预测二审肯定会改判。但我想说的是,尊重法律,审判权是法律的,这也是司法独立的要求。如每一个案件经过舆论的发酵喧嚣都可以成为另一种结果,不论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每个人都会想要成为那种特殊。
免责声明:本网部分文章和信息来源于国际互联网,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学习之目的。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立即联系网站所有人,我们会予以更改或删除相关文章,保证您的权利。


 全国免费咨询热线:
全国免费咨询热线:
 皖公网安备:
皖公网安备:



